回顾昙花一现的大都会布鲁尔博物馆:那些可取与失败之处
时间:2020-07-16 11:06:00 来源:艺术中国

大都会布鲁尔博物馆(图片来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Alex Greenberger
文/
2016年,作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现当代分馆,大都会布鲁尔博物馆(Met Breuer)在开放时,场地是从惠特尼美术馆转租来的,首展名为“未完成:可见的思考”(“Unfinished: Thoughts Left Visible”),展出了各种未完成的艺术作品(包括有意和无意的)。
如今,仿佛命运的捉弄,布鲁尔博物馆也以一种未完成的方式闭馆了。受新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根据上个月的官方声明,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告别之下,该馆将正式转给弗里克艺术收藏馆(Frick Collection)。今年3月,令人瞩目的“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展”开幕后仅向公众开放了九天,展期已被缩短,这里的灯光再也不会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守护之下亮起。
其实,布鲁尔博物馆从未计划永久存在。自1966年布鲁尔大楼完工,惠特尼美术馆就一直占据着这里。2011年,惠特尼美术馆准备搬迁到市中心肉库区(Meatpacking District)现在的位置。大都会博物馆即表示将转租布鲁尔大楼至2023年。三年后,大都会博物馆公布了改造其现代和当代分馆的计划。这个6亿美元的项目一直反复调整,直到2018年9月才确定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放。布鲁尔博物馆像一个试验场 ——去尝试更多的前卫和更广泛的具有全球主义倾向的现代展览,而这些在原有的第五大道的地点是没有的。
布鲁尔博物馆,在由马塞尔·布鲁尔(Marcel Breuer)设计的、盒子形、黑暗且不平整的空间里运营,也有不少成功的热点。2016-17年,它同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Chicago)和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Los Angeles)合办的“克里·詹姆斯·马歇尔(Kerry James Marshall)回顾展”,被认为为近期纽约最好的艺术展览之一。此外,布鲁尔博物馆举办的一些个人专题展,如印度雕塑家穆里纳里尼·穆克吉(Mrinalini Mukherjee)的作品展在去年获得了广泛关注,在此之前她在美国几乎是不为人知的。
纽约的博物馆们往往只为知名的艺术家举办大型个展。值得赞扬的是,布鲁尔博物馆却突破局限,并且获得了全球的瞩目。纽约其它的主要博物馆不太可能为印度艺术家纳斯林·穆罕默德(Nasreen Mohamedi)提供一整层的展区,因为他鲜明、极简的作品在纽约少为人知。同样,对伊朗裔艺术家西阿·阿玛雅尼(Siah Armajani)的挖掘和展示,成功聚焦了一个尚待得到普遍认可的艺术大师。
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展览在布鲁尔博物馆而不是在原来的大都会博物馆举办?这让不熟悉展览安排逻辑之中特殊性的人十分不解。上面提及的展览,以及利贾·帕普(Lygia Pape)和马里萨·默兹(Marisa Merz)的展览,如果在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也将同样出色,甚至将会更为重要。但是,由于大都会博物馆没有清楚地表明和传达布鲁尔博物馆应承担何种角色,所以大都会博物馆似乎尴尬地把一些展览塞给了布鲁尔,暗示着这些展览与大都会博物馆的其他作品区分开来。

2016年,在布鲁尔博物馆揭幕的“未完成:可见的思考”(“Unfinished: Thoughts Left Visible”)(图片来源:JUSTIN LANE/EPA/SHUTTERSTOCK)
极少有尝试来缩短这一差距。布鲁尔博物馆最大的两次展览,“未完成”(Unfinished)和“栩栩如生:雕塑,色彩和身体(1300年至今)”(like life: sculpture, color, and the body)都呈现了跨越千年的艺术气息,但又颇为奇特:例如在“栩栩如生”展览中,我们会发现15世纪的骑马雕像竟然与杰夫·昆斯(Jeff Koons)的媚俗小雕塑在同一展厅中。这两个展览都没有带来太多值得研究的新艺术家,而且都遗憾地倾向于保守的审美主义,即在形式上政治、绘画和雕塑优于视频、摄影和表演,尽管它们在当下如此流行。
对比一下同时期纽约主要的现代艺术机构展览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在“栩栩如生”展览举办的同时:惠特尼博物馆举行了佐伊·伦纳德(Zoe Leonard)的个展,他的视频装置思考着时间的流逝;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推出了颇有影响的安德里安·派普(Adrian Piper)回顾展,直击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以及纽约新艺术博物馆在其三年展上关注后殖民时代的思维方式。在这三场展览构成的语境中,“栩栩如生”听起来倒像个不和谐的音符,表明这个展馆似乎多少有些跟不上时代。
几十年来,大都会博物馆的展览一直有着一种优雅的古典主义,布鲁尔博物馆却在艺术的庄严与一点出格之间取得平衡。惠特尼博物馆在布鲁尔大楼所展示作品时就做到了这一点。例如,在2014年举行的最后一次惠特尼双年展上,佐伊·伦纳德(Zoe Leonard)就将一个画廊中类似光圈的窗户变成了照相机的暗箱。大都会博物馆似乎在这方面没有兴趣,它的多数展览还是暗色调、传统的风格。大都会以1300万美元用于布鲁尔大楼翻新的工程,让人无法察觉到什么变化——博物馆既希望展现过去,但又不敢做些激进的改进以展望未来。
自从布鲁尔博物馆揭幕以来,大都会博物馆成功地调整了其现代和当代展览的策略。2018年,在新上任的马克斯·霍林(Max Hollein)的领导下更加重视新艺术,并与大都会博物馆以及众多的藏品展开对话。去年,瓦格希・穆图(Wangechi Mutu)在博物馆正面的壁龛里展出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雕塑,雷亚安·塔贝(RayyaneTabet)在古代近东艺术展厅(Ancient Near Eastern gallery)展出了从叙利亚掠夺并散落的壁画作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巨大的正厅内展出了加拿大第一位具有克里族(Cree)和爱尔兰血统的艺术家肯特·芒克曼(Kent Monkman)的画作《1851年华盛顿穿越特拉华河》,此画描绘了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与众多原住民乘船穿越充满浮冰的特拉华河的景象。
如果没有布鲁尔博物馆,芒克曼、穆图和塔贝的展览也就不会存在。也许,大都会博物馆需要在它长居的主场之外来进行实验,策划出一些更不同、强大和整体上更加有趣的当代展览。大都会也将继续沿着实验的脉络前进着,就像霍林去年对《纽约时报》所说:“我不想看到当代艺术仅仅局限于几个展厅。”即使布鲁尔博物馆只是其悠久历史中的一个脚注,它仍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未来向前发展的关键所在。
编辑: 审编:admin
中国公益快讯客户端
扫一扫掌握更多资讯
最新最热
公益资讯
订阅栏目
效率阅读
视频直播
影音随行
-

探访科伦坡的街头艺术画廊
发布时间:2025-01-09 14:39 -

第九届中国当日艺术展在河南洛阳启动
发布时间:2025-01-02 16:32 -

“溪岸·大地艺术的交响” 安溪县金谷溪岸文艺村2025艺术嘉年华精彩纷呈
发布时间:2025-01-02 16:30 -

宁夏美术馆开馆 再添宁夏文化艺术新地标
发布时间:2024-12-26 16:05 -

舞剧《天下大足》舞蹈动作高度艺术还原 让造像走下崖壁走上舞台
发布时间:2024-12-19 15:44 -

培源艺术节作品《围雾迷城》首演 用“烧脑”故事探寻人性
发布时间:2024-12-12 16:00 -

“艺术设计跨市域协同创新联盟”在沪成立 培养高素质文创人才
发布时间:2024-12-05 15:36 -

澜湄合作国际艺术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展在老挝成功举行
发布时间:2024-11-28 15:46 -

田沁鑫:让敦煌艺术年轻起来
发布时间:2024-11-14 14:56 -

青海省第十九届摄影艺术展开幕
发布时间:2024-11-07 16: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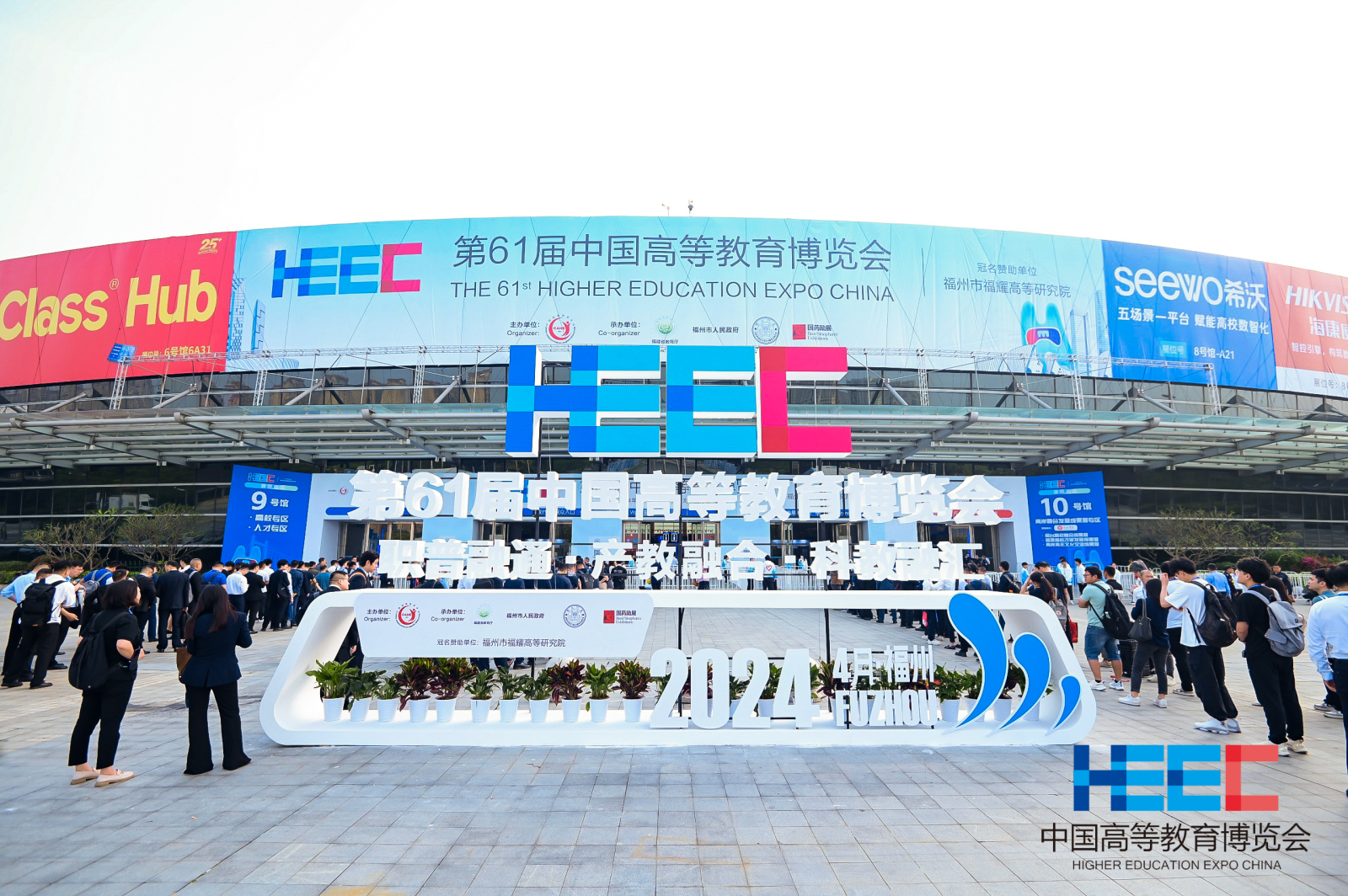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