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几时归去,作个闲人
时间:2022-10-11 10:09:47 来源:凤凰网
虽然苏东坡和我们处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身份,但他和我们一样要面对普通人的烦恼、人生的不确定和命运的无常。他也痛苦过、迷惘过,甚至绝望过,但最终却用一颗旷达的“闲心”守住了心灵的空间,消解了所有的磨难,活得快乐且通透。
“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是苏东坡一生作为闲人的最好写照;“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是苏东坡最简单的快乐指南。在下文作者费勇看来,“东坡”的意义在于:“人应该拥有一块自己的天地,哪怕是很贫瘠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你要自食其力,做自己想做的事,让生活升华为一种诗意的境界。”
本文摘选自《作个闲人》,经出品方授权推送。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苏轼《行香子·述怀》
一、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人生有很多烦恼,假如你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去找苏东坡聊天,想让他开导一下,他多半不会和你讲什么道理,而是随手拿起一壶酒,一起喝了再说。或者请你弹琴,或者拉着你去楼下的草地上躺下看云。生活中的烦恼,靠想可以想开一点,但更应该靠体验,去体验一件很美、很细微的事,在体验之中让心胸慢慢变得广阔。
那么,为什么要用琴、酒、云呢?
第一,这三种事物都是一种有形的东西,能够看见、听见、触摸。最关键的是能够让你去做具体的某件事,即弹琴、喝酒、看云。
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必需品。我们的家必须有烧饭的锅,必须有睡觉的床,起床了必须穿衣服,必须出门去工作,必须每天喝水,但不一定需要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它们都属于无用之物,属于业余爱好。
不是必须,却是应该。不是你必须做的事,却是你应该做的事。
吃饭,不用别人说,你也一定会吃,不吃会饿。但弹琴之类的事,你可以不做,不去做也不会怎么样,但你应该去做,因为做了之后,生活就会有所不同。
喝酒的真正意义在于,让你学会节制、学会平衡,从而变得更好。
弹琴是欲望的升华、净化,会让你变得风雅。看云是把个人融入大自然,会让你变得有趣。喝酒是承认欲望,承认肉体的愉悦,在妥协中达到微醺,可以马上疏解你的痛苦,但也会伤害你,让你失控。
所以,这三种事物,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思。
第二,这三种事物,不单单是一个孤立的器具,而是一个场景。
弹琴、喝酒、看云,都是一个场景,不仅是场景,还是一个爱好体系。
琴、棋、书、画是传统中国最典雅、最广泛的业余爱好,写作、阅读也可以归入其中。这些事情可以陶冶性情,可以让人心平气和,属于心灵层面的事情。
“一壶酒”代表着包括茶在内的美食体系,养生也包括在内。这个体系里的事情可以给人带来愉悦和陶醉,可以让人身体安康,属于身体层面。
“一溪云”代表着自然风景体系。苏东坡特别喜欢月亮,也喜欢海棠和梅花,喜欢旅行,喜欢在自然里感受季节的变化。
如何构建出我们的生活美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生活中营造这三个体系:业余爱好体系、美食体系、自然体系。这三个体系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一点盐,让人变得更有品位、更有趣味。
第三,这三种事物背后,包含着一套价值观。
琴,代表音乐,儒家讲“礼乐”,这个乐,就是音乐。可见音乐在儒家心目中有多么重要。孔子喜欢音乐,曾经在齐国听韶乐,沉醉其中,三个月都不知道肉的味道。
孔子有一句话很有名:“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大意是人的成长开始于学习诗,自立于学习礼,完成于学习乐。当我们把琴棋书画、写作等包含在“一张琴”里,意味着“一张琴”涵盖了成长的整个过程。
关于酒,古代希腊有酒神的传统。《庄子》关于酒的一个说法也颇耐人寻味:
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
醉酒的人从车上掉下来,虽然满身都是伤却没有死去,他的骨骼关节跟别人一样,但受到的伤害却不同,为什么呢?是因为醉酒以后忘掉了外在现实,忘掉了对死的恐惧,因此,外物就伤害不了。庄子用了一个词:神全。醉酒的人,“神”是全的。这是透过非理性、直觉来探寻生命的本原。

关于自然,儒家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道家说“道法自然”,佛教说“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翠翠青竹,总是法身”,又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
儒、道、佛都认为人类应该和自然和谐共处,儒家上升到天命、天理,道家上升到返璞归真,佛家上升到觉悟成佛。
“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不是必需品,是随手可得的审美之物。一旦我们把它们融入生活,就会带来一个体系式的场景,带来一套基于兴趣的生活方式
归纳起来,。
而这三种事物在儒家、道家、佛家以及在西方哲学的诠释系统里,都具有形而上的意义。
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都是一,很简单,带来的却是趣味和意义的无限叠加。通过“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最终我们可以从现实烦恼里解脱出来,通向本来面目,也通向自然法则。这就是苏东坡为什么说你需要“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原因。
这不仅仅是爱好,而是一种重组,在重组里为身心找到安顿。
在欣赏之中,在陶醉之中,渐渐找回到本来面目,激发内在的直觉。
喜欢古琴,喜欢阅读,喜欢写作,喜欢喝酒,喜欢看月亮、看云,开始也许是为了缓解压力,但慢慢地,那么,生命就在重组中不断被重新创造,不断突破边界,不断从有限走向无限。
有限的游戏在边界内玩,而无限的游戏玩的是边界,是对于边界的突破。
詹姆斯·卡斯认为存在着无限和有限两种游戏,有限游戏的目的是赢得胜利,而无限游戏的目的是让游戏一直玩下去。有限的游戏具有确定的开始和结束,而无限的游戏没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没有赢家和输家,可以一直玩下去,而且可以把更多的人带入游戏。

“作个闲人”把人从有限的游戏里解放出来,进入了无限的游戏。
苏东坡“作个闲人”以“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作为媒介,建构了一种无限的游戏。如果说官场或者现在的职场是有限的游戏,那么,
“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运用的不是宏大的观念或体系,而是一些微小的,甚至微不足道的事物。这让我想起卡夫卡的一则日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一天,卡夫卡在日记里写了这么一句:“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
面对巨大的时代变故,卡夫卡用了一个破折号表达了一种坚持,坚持自己的闲情逸致。
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说:“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就三样:自由、平等、蟹肉汤。”把蟹肉汤这么日常的食物和自由平等放在一起有点奇怪,但哲学家齐泽克觉得“蟹肉汤”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自由”,他把蟹肉汤解读为“生活中所有精致的乐趣”。
一旦失去这些小确幸,我们就会变得与恐怖分子无异
——我们会沦为抽象观念的信徒,并会丝毫不顾具体情境地要将这些观念付诸现实。
苏东坡的“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所具有的意义和“蟹肉汤”是一样的,也是以“闲情逸致”来抵御现实的平庸和束缚。经历乌台诗案之后的苏东坡,刚到黄州,就写下了这么两句诗: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
风景和美食,这样的小确幸,让苏东坡从时代的洪流里抽身而出。

二、适然而已
“作个闲人”,“闲”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闲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
苏东坡流落在黄州,开始时还幻想着不久就能回到京城。很快,他就绝望了,决定在黄州安顿下来。有一个老朋友帮了他的忙,把一块官府废弃的荒地给了他。那个地方在东边的坡上,正好苏东坡喜欢的白居易在忠州时喜欢在东坡上种花,所以,苏东坡就把自己黄州的那块荒地叫作“东坡”。
他还为自己取了一个号“东坡居士”。古人的名和字是父辈取的,但号是自己取的,从古人的“号”上可以看到他内心向往哪一种生活,看出他的价值观。
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居士是佛教的在家修行者。可以看出,到黄州后,苏东坡喜欢上了佛教,甚至想要去修行。
而“东坡”意味着他要学陶渊明,过一种田园生活,在这里种地、读书、写字、画画、弹琴、喝酒。他写了一首词《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这首词的前面有一段说明,大概意思是,当年陶渊明在斜川游玩,流连忘返,于是写了《斜川诗》,至今还让人神往。我现在也回归田园,在东坡耕种,还建了东坡雪堂,四面的风景很怡人,和陶渊明的斜川有同样的韵味。
在词里,苏东坡说,能够做着梦又很清醒的,能够越喝酒越清醒的,大概只有陶渊明吧,他是我的前辈,也是我的知己。我在人间历练了一番,如今还是回到田园耕作。
昨夜东坡下了一场春雨,鹊鸟鸣叫着,预示着今天天气晴朗。雪堂西边的山石间一道幽泉流水潺潺,北山微微倾斜,还有小溪横流在山间,再向南边的四望亭小山丘望去,独特的美景好似当年陶渊明笔下的曾城山。我已经老了,剩下的岁月就在这里这样度过吧。

陶渊明辞官归隐田园,是主动的选择。他写了很多描绘自己劳动的诗歌,比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陶渊明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桃花源”,“桃花源”成了人们理想生活的代名词。“桃花源”里没有神仙,没有菩萨,也没有圣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都是些平平淡淡的日常,但这里没有改朝换代,没有权力斗争,只有岁月静好。
“桃花源”里的生活是一种不被打扰的生活,一种不违心的生活。陶渊明开创了这种生活的基调,却缺少系统和丰富的细节。“桃花源”就像一种召唤,又像一幅很治愈的画面,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沉淀在内心的一种向往。
苏东坡去黄州,不是主动的选择,而是身不由己。但在身不由己中,苏东坡在黄州开荒,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耕田种菜。他还建了东坡雪堂,呼朋唤友,吟诗作画,喝酒听曲,创造了自己的桃花源。
“东坡”的意义在于:人应该拥有一块自己的天地,哪怕是很贫瘠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你要自食其力,做自己想做的事,让生活升华为一种诗意的境界。
虽然苏东坡很谦虚,说自己不如陶渊明,还在世俗事务里“缠绵之”,但在我看来,恰恰这个“世事缠绵之”,使苏东坡更具有当代性,也更深刻。

从桃花源到东坡,是中国式“治愈主义”生活方式的一个完成。苏东坡把一种向往变成了现实。所以,桃花源一直就是桃花源,是一个诗意的地理概念。而“东坡”由一块荒芜贫瘠的山坡,变成了一个人名,一个最治愈中国人的人名。
“东坡”,显示了一个普通人在世俗生活里所能达到的最高生活境界。
苏轼还给自己取过另外一些“号”,比如东坡病叟、雪浪翁、毗陵先生、东坡道人、铁冠道人、老泉山人等,从他的这些号里可以一窥他的心路痕迹。在中国的文人里,苏东坡为自己取的号最多,别人称呼他的号也最多。
一方面说明他从未停止过自我探索,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给人的印象的多面性。但他最被接受的号还是“东坡”。
当然,最重要的是,苏轼成为苏东坡之后,他和世界那种紧张关系被转化了。甚至可以说,当“东坡”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传统中国文化的美妙哲理一下子就在日常生活中盛开成花朵,不再是教条,而是生动有趣的生活。
在这本书里,我全部用“苏东坡”这个名字,是因为我觉得“东坡”这个名字本身已经涵盖了我想在这本书里阐述的核心思想。更重要的是,就生活而言,“东坡”是一个比“桃花源”更意味深长,并具有实践性的意象,体现了中国式治愈主义的观念系统和行为系统。
在《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这首词里,提到了“雪堂”。
这是苏东坡在东坡视野最好的一个地方,自己设计的一个空间,用来接待朋友。建好的时候,正好下雪,所以在墙上画满了雪景,取名雪堂。坐在里面,感觉四面都是雪。

苏东坡有一篇散文叫《雪堂记》,说是有一天,他在雪堂里刚刚睡醒,有个朋友来到这里问苏东坡:“你在世间是一个闲散的人,还是一个拘谨的人呢?”所谓闲散的人,就是不受束缚,自由任性的人;拘谨的人,就是受到各种束缚,放不开自己的人。
苏东坡还没有回答,这个人就给苏东坡下了结论,你是想做闲散的人而不得。然后,这个客人就说了一通怎么达到闲散的道理,又批评苏东坡以为躲在雪堂,就是跳出了世间的藩篱,就可以安顿自己的身心,这其实是一种妄念,而且仍在危险之中。
苏东坡明白这个人说的意思,但是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觉得在雪堂生活已经可以了,没有必要再去更远的地方。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说:
予之所为,适然而已,岂有心哉,殆也,奈何!(《雪堂问潘邠老》)
意思是“我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求个适意罢了,哪有什么用心?怎么能说我就危险了呢?”又说“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意思是“我并不想逃避世上的事物,只是想躲开世上的机锋”。
苏东坡只是求个适意罢了,并不是想逃避世界上的各种事情,只是要逃避现实里的各种算计、各种钩心斗角。
作个闲人,不过就是做个适意的人,做一个自然而然的人。
这才是苏东坡要表达的“作个闲人”最本质的意义:
苏东坡评价陶渊明:
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想当官就去当官,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不想当了就不当,也不会觉得不当官了就有多么清高。饿了就敲邻居的门要点吃的,吃饱了就杀鸡宴请宾客。所以,从古到今的人都喜欢他,因为他做人很真实、很率真。
这应该就是苏东坡心目中“闲人”的形象。
当然,在苏东坡的观念里,“闲人”不应该是一个教条式的观念,而是一种生动的姿态。“闲人”不是由观念规定出来的,而是在具体的生活里活出来的,是鲜活的形象。

三、东坡的弥留之际
通过一个故事,我们来了解一下苏东坡对于死亡的看法。
有一次,退休副宰相韩维的女婿拜访苏东坡,聊起他的岳父,说韩维退休后沉迷于宴饮享乐。
苏东坡听了不以为然,说老了更加不能这样。然后,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老人,临终之前把子女叫到身边,告诉他们:“我就要离开人世了,我只有一句话要留给你们。”子女问:“什么话呢?”老人说:“每天五更就起床。”
子女们很困惑,我们家那么富裕,为什么要起早呢?老人就说:“五更起来,可以做自己的事,太阳出来后,想做自己的事就很难了。”
子女更加困惑,自己的事什么时候都能做啊?家里的事不都是自己的事吗?老人就说:“我说的自己的事,是死的时候能带走的。你们看我赚了万贯家财,死的时候都带不走,那我死的时候能带走什么呢?”
苏东坡说完这个故事,就对韩维的女婿说:“请转告你岳父,越是到了晚年,越是要做自己的事。与其在声色犬马里消耗生命,不如多想想死的时候可以带走什么?”

为什么故事里老人说“五更起来,可以做自己的事,太阳出来后,想做自己的事就很难了”?为什么要自己独处的时候,才能做死后能带走的事情呢?
苏东坡临终之前的一番话也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1101年8月24日,苏东坡弥留之际,维琳法师在他耳边说:“端明宜勿忘西方。”
苏东坡曾经是端明殿学士,“端明”是对苏东坡的尊称,维琳法师是在提醒苏东坡不要忘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苏东坡轻声回答:“西天不无,但此中着力不得。”(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没有,但不应该刻意用力。)
他的朋友钱世雄在旁边劝导:“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先生您一直在践行于此,此时更应该用力。)
苏东坡回答:“着力即差。”(用力就错了。)
佛教徒的苏东坡相信西方极乐世界,但他认为去往西方极乐世界,不应该用力,更不应该刻意。
那么,死后他要带去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苏东坡去世前两天,也就是 8 月 22 日,写给维琳法师的一首诗中可以找到答案: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
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苏轼《答径山琳长老》
我和你都是丙子年出生的,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过了三万天。就算每一天说一千句偈,时间也像电一样一闪而过,不容置疑。

人的忧患在于有身体,如果没有身体,就没有什么疾病。鸠摩罗什虽然是一位高僧,但好像还没有看透,临终前让弟子念西域的神咒,但念诵的仪式还没有完成,他就去世了。
苏东坡对于死亡,始终保持着一种坦然的态度。因为死亡不可避免,无论你怎么保养,怎么祈祷,人都会死亡。至于死亡之后是不是能够去极乐世界,苏东坡是抱着自然而然的态度,不赞成刻意追求去极乐世界,他觉得顺其自然就好。顺其自然,就是接受死亡;顺其自然,就是回到自然的本源,回到本来面目,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仔细体会一下苏东坡的意思,死后,人世间的东西我们什么也带不走,西方世界不是有形的东西,也是一种妄念。
我们真正能够带走的,或者说,我们能够进入的,是回到我们本来的样子。我们本来的样子是什么呢?就是《心经》里说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是空的境界。
换一种说法,一旦我们放下执念,我们就能够回到自己本来的样子。这才是死后能够带走的。
做一个自然而然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一个理性的人。
苏东坡说,要作个闲人,最终极的意思是做一个活在空性里的人。这听起来有点玄,但在苏东坡的人生实践里变得很简单,就是
有一次苏东坡坐船遭遇逆风,船很难前行,他点了香向着僧伽寺祈祷,结果风向就变了,变成了顺风。但后来,他又遇到了逆风,却不愿再求神拜佛。为什么呢?
耕田的人要下雨,收割的人要晴天;离去的人要顺风,来的人又对逆风抱怨。如要让人人祈祷都如愿,老天爷岂不是一天要千变万化?也就是说,如果满足了我的愿望,那一定会让别人满足不了愿望。
所以,苏东坡说,从此以后——
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
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
——苏轼《泗州僧伽塔》
我如今自身和世俗两不相关,去无追求,来也无所留恋。能走得快些固然很好,走不了无所谓,假如每次有所求的时候就去求神,神也会厌倦。
“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确实是苏东坡一生作为闲人的最好写照。
编辑:王俊杰 审编:admin
中国公益快讯客户端
扫一扫掌握更多资讯
最新最热
公益资讯
订阅栏目
效率阅读
视频直播
影音随行
-
第七届“青海年·最海东”文体旅游系列活动启动
发布时间:2024-12-26 16:04 -

哈工大冰雪体育课“燃动”上线
发布时间:2024-12-19 15:42 -

“每天一节体育课”落地观察
发布时间:2024-12-12 15:59 -

小区文体广场设施损坏问题得到迅速解决 --淄博新闻网
发布时间:2024-12-05 15:34 -

汉江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支教捐物”活动在东风二中举行
发布时间:2024-11-28 15:45 -

“文体惠享”项目提前超额完成目标
发布时间:2024-11-21 14:31 -

第六季朝阳职工文体嘉年华职工乒乓球比赛圆满举办
发布时间:2024-11-14 14:55 -

贵师大2024年体育文化艺术节开幕
发布时间:2024-11-07 16:44 -

水韵江苏·美好生活|镇江世业洲:让“农文体旅”融合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发布时间:2024-10-24 14:54 -

沈阳发布六大主题370余项秋季文体旅活动
发布时间:2024-09-04 15: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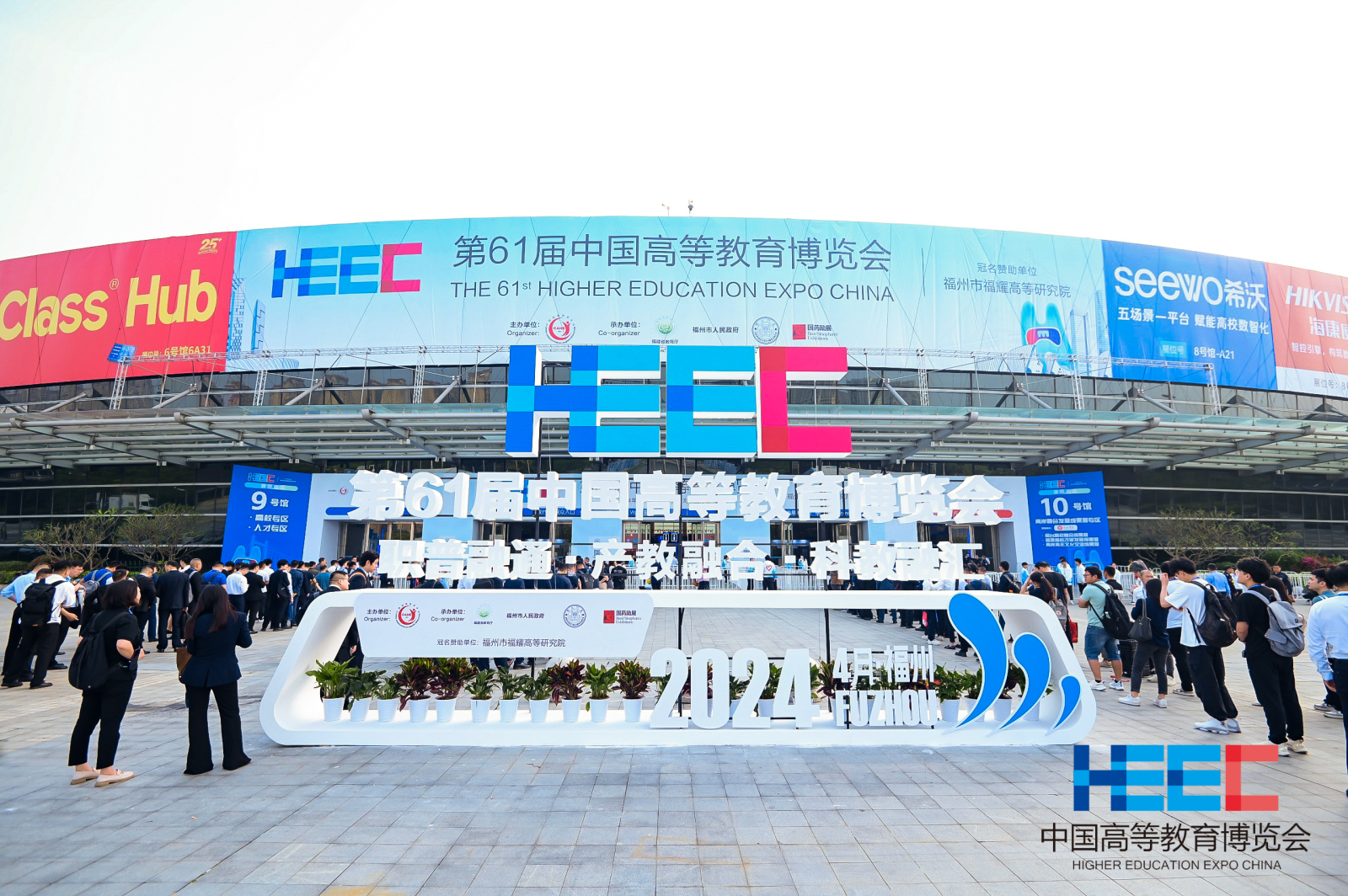


网友评论